作者杨本科
由黄花梨制成的小件器物,多为笔筒、扇骨等,都是文房清供。文房清供是指书房的陈设器具,及与笔墨纸砚相应发展而来的各种辅助用具。书房本身就是读书人的天地,文房清供又是独属于读书人的东西,既是赏玩之物,又是读书之需。宋朝真宗以皇帝之尊,写诗诱导人读书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都是需要读书人“释褐”才能实现的——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承者,所以,那个高雅文雅的“雅”,大多属于读书人。黄花梨清供与文人朝夕相伴,自然也就成为文人雅趣的承载者。
花梨木为斫琴之妙术
“花榈,又名花狸,亦作花梨,海南文木之贵重者。”因其细致坚硬的质地、幽幽的香味、柔美的纹理和较小生长地理范围、较长生长周期而珍贵。人们早就知道“(黄花梨)出海南,紫红色,与降真香相似,亦有微香,其花有鬼面者可爱”,富豪之家尤为珍视。清人吴允嘉把严嵩父子抄家时候的财物清单专门记录下来,合为《天水冰山录》一书,竟有六万多字,其中便有玉厢花梨木镇纸一条、花梨木镜架一个、花梨木鱼一个、小花梨木盒一个、花梨木锥一件、素漆花梨木凉床四十张,足可证明严嵩父子之贪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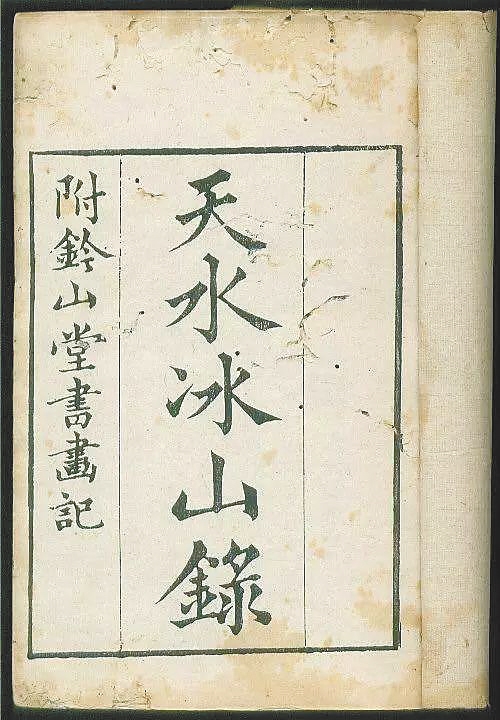
《天水冰山录》。
据宋代琴学著作《琴苑要录》记载,制作古琴,如果选用梓木,就要避开树心,因为“太硬则声细而浊,太璁则声透下而响”。当时人们要求木料“惟要紧缓得所,木性条直,阴阳相向,底面无节,是为斫琴之妙术也”。琴上焦尾、临岳及贴池木等构件,用降真香或紫檀金线木,但是当时这些木料都不容易得到,“用花梨木,或深紫色者代之,亦可也。”明人抄宋书,有夹带私货的嫌疑,但这至少也能说明,花梨木早就走进了文人雅士的生活。
朝鲜哲学家北京购买黄花梨笔筒
乾隆时期,祭神祭天典礼的器具中,就包括花梨木雕龙大柜、花梨木拍板、花梨木方盘桌等,朝鲜文人李海应随使团来华,看到“宫室椅桌棺椁之材,盖非椵非楸,细理坚韧,非松杉之比。花梨、紫檀、降真、沉香、乌木等器,多是贵家物”。据此看来,其价格绝非普通人所能接受。

明代黄花梨琴案。 王世襄旧藏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
朝鲜著名汉学家柳得恭在其《燕台再游录》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申濡和琉璃厂聚瀛堂老板崔琦的一件小事。有一次,崔老板送了一把杭州纨扇给他,上面画着草花蛱蝶,用花梨做柄,“卍”字文锦饰边。申濡说,这把扇子极其雅美,是不是西湖畔翠袖低唱之人所持之物?崔琦说,这一把不是,你想看看“西湖畔翠袖低唱之人”拿的是什么吗?接着掏出一把圆扇,以玳瑁为框,以象牙丝为面,以珐琅为柄,以金银为装饰,草花蝴蝶扇面是用象牙染刻的,用来遮面,但依然可以透视外面。价值十两银子,折合朝鲜货币为四十两。申濡不禁感叹——朝鲜哪有人能花四十两钱买一把扇子的呀,过去把西湖叫作“销金涡”,看来是真的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海南的花梨木在北京愈发出名,清人翁方纲见到《黎俗图》写有“其木蕉椰杂榛菅,桄榔木棉夹斑斓。沉香黄黝花梨斑,周植井落城邑间”。当时朝鲜哲学家李朝、自然科学家洪大容和许筠同行,逛到北京隆福寺大雄殿前,见到有人售卖文房雅具。许筠要买一个黄花梨笔筒,老板要价是十几两银子。两人扭头就走,老板就把他们喊回来,说价格好商量。反反复复六七次,最后以一两二钱的价格拿下。洪大容不由得感慨说,真是“天下老鸦一般黑!”
文人们的黄花梨雅趣
黄花梨除了花纹美观,其质地坚硬,更是有着非常实用的价值。两江总督李星沅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了一件事,说他的朋友往日曾在台湾做官,“(台湾岛)气候甚暖,五谷四时皆熟,民多殷富。冬月不裘,元旦贺节有衣絺綌者,但俗名荷叶地。每三五日一动,卧榻前皆置一桌,以花梨、紫檀为之。如地动时,房屋坍塌,人即避于其下。”今天我们也说,地震来临的时候,可以就近躲在“坚固的家具旁”,而花梨木家具显然满足这样的要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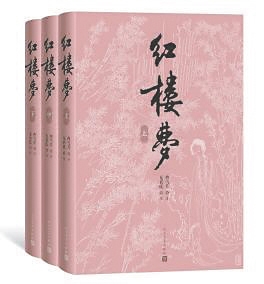
《红楼梦》。
收藏家一般认为花梨、紫檀于明隆万时期开始流行,一发不可收拾。文人们也凑了兴,把黄花梨风行的盛况直接写进他们的文学作品中: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的“孙行者大闹黑风山”中描写孙悟空出门去找黑熊精,路上遇到给金池长老送请柬的小妖:“正行间,只见一个小怪,左胁下夹着一个花梨木匣儿,从大路而来。”曹雪芹在写《红楼梦》时,对花梨木也多有提及,第四十回“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”、第六十三回“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”、第八十一回“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,右边堆下两套旧书,薄薄儿的”、第九十二回“那小厮赶忙捧过一个花梨木匣子来。大家打开看时,原来匣内衬着虎纹锦,锦上叠着一束蓝纱”等等。而自明清以来,小说中描述家具之奢侈,如《孽海花》《儒林外史》等,亦是多处提及花梨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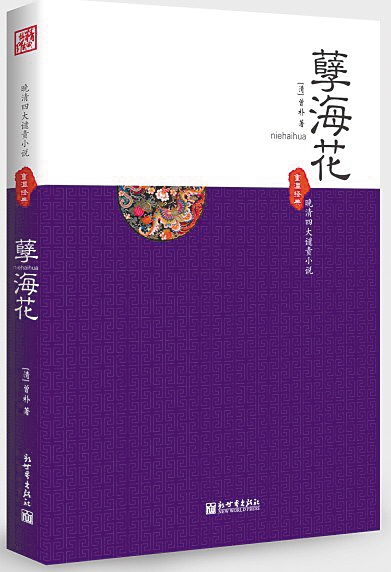
《孽海花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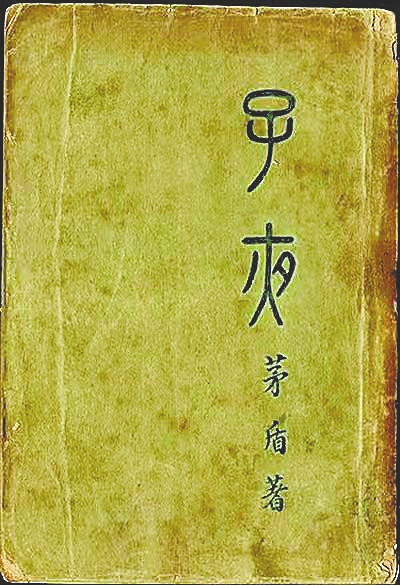
1933年版《子夜》。
值得一提的是,1935年,茅盾的小说《子夜》出版,书中人物张素素一次“摇头不作声,闷闷地绕着一张花梨木的圆桌子走”,又一次“似乎感到更悲哀,蹙着眉尖,又绕走那张花梨木的圆桌子了”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片段,就好像今天我们可以写一个“望着无名指上的鸽子蛋发呆的新娘”一样,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一个富贵的物象。以至于1948年国华编译社翻译《飘》的时候,床榻、首饰盒、针线盒的材质都翻译成了花梨木。
在前人的生活中,黄花梨制品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,这种价格上的区隔,使得花梨木进入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天然的陌生感,意味着神秘、高贵。而形制上的传统,使得黄花梨家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,又构成了一个神秘、富贵与古板的两面性的物象,值得玩味,在家具中能扮演这个角色的,恐怕不多见。而更值得玩味的,是作家们在文字之外的哲思与雅趣。
原标题:
文人雅士与黄花梨:清音雅趣载哲思

责任编辑:曾敬
内容审核:樊学玲
值班总监:史雅洁
值班主任:张成林

全部评论 ()